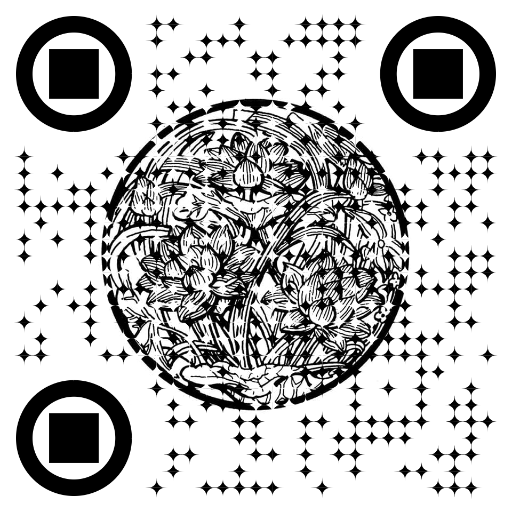(一)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的转型历程
欧盟一贯重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一般采取立法的形式将特定时期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设定为支持目标,实施针对性策略解决新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长期探索和多轮改革,欧盟已经形成了兼具目标综合性和手段综合性的共同农业政策。
欧盟国家从1962年开始通过以农产品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共同农业政策”调控农产品市场。为了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保障农产品稳定供应,欧盟制定了一系列共同价格并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共同价格的制定和围绕这些价格的市场干预,是共同农业政策价格干预机制的基本内容和手段。共同农业政策价格机制主要包括目标价格、干预价格(Intervention Price)和门槛价格三类。目标价格是依据某种农产品在欧共体内部供不应求地区的市场价格而定(包含贮藏费和运输费),几乎涵盖所有的农产品,是共同农业政策规定的农产品市场最高价格。
干预价格是农产品在欧盟销售的价格下限,运行机制十分类似于我国临时收储制度。当某类农产品供过于求,出现相对过剩,市场价格低于干预价格时,生产者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后可以从欧盟设在各成员国的干预中心领取市场价格与干预价格之间的差价补贴,或者将农产品以干预价格直接卖给干预中心,干预中心收购的谷物可以储存起来待价格回升后再投入市场, 加工处理制成饲料或工业原料。干预价格保证了农业生产者收回生产成本并获得微利,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因而干预价格也叫保证价格或保护价格,一般比目标价格低10%~15%。
门槛价格针对欧盟之外的第三国而设立,其目的是鼓励消费者优先购买欧盟内部的农产品,如果第三国农产品到岸价格低于门槛价格,就征收这两种价格之间的进口差价税,进口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甚至高于目标价格,因为除门槛价格外,还有贮藏费和运费在内,因而失去了价格竞争优势,欧盟内部农产品贸易得以保护。一般而言,当市场价格在共同价格限定的范围内自由波动时,欧盟并不进行干预;一旦超出此范围,欧盟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干预使之回归既定的价格区间。
欧盟国家早期以政府价格干预为主的农业支持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有效调动,农产品产量因而迅速提高,由短缺转变为盈余。然而,也带了很大的问题,如加重了欧共体国家的财政负担、农产品由于价格过高而丧失了竞争力、消费者的食品支出增加过快、农产品贸易环境不断恶化以及农业生产环境遭受破坏等。共同农业政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补贴政策导致农民盲目扩大生产,造成产品供大于求,农业预算压力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欧盟。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强烈批评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扭曲了世界市场的价格,导致与贸易伙伴的严重冲突,制约和阻碍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随着农产品生产逐渐过剩、农业竞争力下降、生态环境和国际贸易等问题的渐次出现,欧盟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多轮改革,通过逐步削减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水平以降低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构建以直接补贴为主的农业支持政策以替代价格干预政策的收入支持功能,完成了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支持政策的战略转型。
1992年麦克萨利改革开启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战略蜕变,欧盟开始削减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水平,如将谷类价格降低29%、牛肉价格降低15%等;同时,将直接补贴农民收入列为农业支持政策的核心内容,并加强对中小型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支持。此次改革以挂钩直接补贴替代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降低了主要农产品的支持价格水平并减少了获得价格支持农产品的数量,减轻了价格扭曲, 农产品库存水平较大幅度下降,缓和了欧盟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 与此同时挂钩的直接补贴保障了农民收入不受价格支持政策削减的影响。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期WTO 农产品贸易谈判要求以及美国、凯恩斯集团国家等的压力逐渐增大, 欧盟在《2000年议程》强调对农业政策进行更为彻底和全面的改革,计划分步骤、分阶段地削减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如3年内削减谷物和其他重要农作物的支持价格15%等。
2003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进一步降低农产品支持价格,进一步向农产品市场化迈进,如2004年谷物干预价下浮5%,黑麦从干预体系中移除等;同时废除将农业补贴与农产品产量挂钩的做法,实行与产量和种植面积无关的脱钩补贴,从而避免WTO黄箱政策“微量支持” 的限制。与此同时,欧盟将支持农村地区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重点。一方面增加了农村地区发展支持力度, 将削减的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预算转移至农村发展项目(第二支柱项目);另一方面引入了交叉遵守机制,将农业补贴资金的获取与农业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等挂钩,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2013年年底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延续了市场导向的改革路径,对农村经济、生态环境和成员国区域平衡发展等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提出了增强农业竞争力、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以及成员国区域平衡发展等三大长期目标,并制定了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二)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转型历程
美国农业的特点是农产品长期生产过剩,且十分依赖国际市场。一旦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供过于求, 美国就会面临生产过剩危机,同时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也会对美国农场主收入带来不利影响。因而, 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应对国内农业生产形势和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变动,以保障农场主利益。农业法案是美国政府实现上述目标的政策工具载体。
早期的农业政策以价格干预作为保障农场主收入的主要手段。20 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促使美国政府通过了第一部农业法案《农业调整法》,形成了其农业支持政策的雏形。美国政府通过构建农产品储备调控体系和实施销售贷款补贴以解决农产品生产过剩和价格不断下降问题,从而保障农场主收入。20世纪50年代,国际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美国政府开始全面提高价格支持水平,此后不断调整和扩大农产品补助范围并于1977年开始全面推行目标价格补贴制度。价格干预政策缓解了农产品过剩危机给农场主收入带来的损失,保障了农场主的收入。然而,上述干预政策不仅扭曲了农产品市场价格,难以反映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而且带来了过量的农产品储备,加重了政府的巨额财政负担。此外,农产品价格维持在最低保护价格水平上,导致农产品进一步过度生产。
1985年的《食物安全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开始进入现代市场化导向的农业法案时期,逐步形成以收入补贴为主要手段的政策体系。市场化的改革肇始于20世纪80 年代初期美元升值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农场主收入水平下降,以及同时期政府财政难以维持高昂农产品补贴。在综合兼顾农场主利益和财政预算压力后, 1985年农业法案削减了价格支持水平;通过鼓励和补贴土地休耕等手段限制生产的扩张以及补贴流通环节以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农产品价格水平;同时开始采用市场手段(即“无追索权贷款”)实施销售贷款补贴,以解决国家农产品的过量储备问题。
受20世纪90年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谈判的影响,1990年的《食品与农业贸易保护法案》深化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如与全球农产品市场价格连接,以85%的耕地面积作为政府差价补贴的基础,其余15% 的耕地面积不再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农民可根据市场状况自由调整生产结构和规模;逐渐将价差补贴的市场价格由原来的5个月市场平均价格改为12个月市场平均价格。在1995年前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增强、全球经济增长良好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制定了有史以来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农业法案——1996年《联邦农业促进与改革法案》。该法案强调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水平、逐步采取与产量脱钩的直接补贴以降低市场干预程度。
然而,随着21世纪初期的美元贬值、国际农产品生产价格下跌、农场主农业收益下降、联邦政府预算出现盈余,欧盟、日本等国家的农业补贴水平逐渐提高。2002年的农业法案的目标为农场主“提供可靠的收入安全网”,在继续实行1985—1996年间的“农产品计划” 和“环境保护计划”、强调补贴同产品生产脱钩的同时,将“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同“销售贷款补贴”一起形成农民收入的安全保护网。2014年的农业法案对农业补贴政策的价格与收入政策、农业保险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大幅调整,强化了农场收入安全网的建设。
(三)欧美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共同特点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导向十分明显。欧美发达国家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调整与演变,其驱动因素不仅来自国内农业发展需要,而且来自于国际贸易伙伴和国际贸易组织的压力。尽管在政策发展过程中有所反复,但总的趋势是朝着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政策演变。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和美国的农业法案从早期的价格干预政策发展到脱钩的直接补贴进一步转变为脱钩的直接补贴政策,经过了漫长复杂的发展过程。如欧盟和美国均在WTO农业协议框架下,适时调整和优化农业补贴政策,将农业补贴方式逐渐转向更为符合WTO规则的“绿箱”政策,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十分明显; 美国对棉花生产者的补贴由“黄箱”政策转向以农业保险为主的“绿箱”政策,而欧盟更是以实行脱钩的直接支付政策避免WTO相关规则的约束。
其次,在削减价格支持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保护农场主的收益。欧盟以农民收入为转型支撑点,多元化农民收入是其农业支持政策转型的关键,体现为农民市场收入(价格支持)、直接补贴收入、非农收入和生态保护收入等多元收入源的增设和巩固,农业环境保护付出与收入增加的兼顾。欧盟以收入、地区发展支持扭转农民间、行业间、地区间收入悬殊, 以农产品就地加工等非农就业、增益性生态服务奖励来增加收入源, 留住农民的同时实现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并按收入流向有针对地支持青年农民以保持职业的继承。就美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而言,从通过单一的价格支持政策逐步向直接补贴、价格支持、农业保险等农民收入安全网体系建设,保障了农场主免于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的冲击。美国在长期的政策演变过程中,逐渐提出并构建了安全而可靠的“收入安全网”,并且工具逐渐趋于多元化和绿色化,如从价格支持到收入支持,再到贷款补贴和保险计划的支持。
第三,欧美国家农业支持政策转型过程中政策工具绿色化水平逐渐提高。WTO《农业协定》是规范各成员农业支持与补贴措施的准则。《农业协定》按照农业支持政策工具对市场的扭曲程度将各成员农业支持和补贴措施分为“绿箱” 政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绿箱”政策没有或者仅有微小的扭曲作用、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小,因而成为WTO《农业协定》的鼓励方向。从欧美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的转型经验来看,其农业支持政策绿色化水平均逐步提高,政策工具选择从严重扭曲市场的价格支持政策转向与农业生产挂钩的直接补贴政策,再从挂钩的直接补贴政策向脱钩的直接补贴政策,进而向农业保险、基础设施建设以农业技术推广等“绿箱”政策转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1年第12期
 首页
首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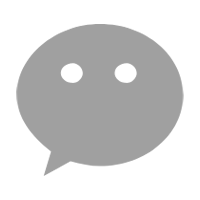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